
-
 专利
专利 -
 商标
商标 -
 版权
版权 -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
 反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 -
 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 -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 -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律师动态
更多 >>知产速递
更多 >>审判动态
更多 >>案例聚焦
更多 >>法官视点
更多 >>裁判文书
更多 >>摘要:文学角色借用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创作手法,有其美学依据和文化价值。为了达到借用的互文效果,只要借用角色名称、被借用的作品有一定知名度、能够唤起读者对被借用作品的联想即可,无须复制被借用作品的表达。这种最低程度的借用既不侵犯著作权,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在现有法律规则之下,文学角色借用自由与著作权保护可以兼顾。
关键词:文学角色 著作权 不正当竞争 文化多样性
目次
1 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角色借用
2 文学角色借用的美学依据和文化价值
2.1 接受美学
2.2 互文理论
3 文学角色借用规律与司法裁判的冲突
4 最低限度文学角色借用的合法性
5 结语
在创作中借用在先文学作品已有的角色,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学现象。近年来,这种现象在知识产权界的讨论中常常被冠以“同人创作”或“同人作品”之名。不过,“同人作品”一词译自日文,其中的“同人”原指“同好,有共同爱好的人”,即某部作品的爱好者们用该作品的角色继续创作的新作品,故“同人作品”的英文对译是“fan fiction”或“fanwork”,可直译为“粉丝小说”或“粉丝作品”。在我国知识产权界讨论的语境下,“同人”实际上转化为字面含义,即“人物(角色)相同”,“同人作品”也就是角色与已有作品相同的作品。例如,有判决把“同人作品”定义为“一般是指使用既有作品中相同或近似的角色创作新的作品。”[1]本文不采用“同人作品”的表述,出于几点考虑:1、“同人作品”有其本来含义,如果要转义为“人物(角色)相同”,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表述为“角色借用”;2、“同人作品”概念的出现较晚,容易使人狭隘地理解为只是一种“粉丝文化”现象或后现代的狂欢,而角色借用作为一种文学手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同人作品”之表述,容易遮蔽这种历史。此种遮蔽,使裁判者难以全面地认识文学角色借用的正当性。例如,有判决认为,若“同人作品”创作仅为满足个人创作愿望或原作读者的需求,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可被容许的,还指出被告最初的创作动机是“出于好玩的心理”。[2]显然,“个人愿望”和“原作读者”的限定都表明,“同人作品”被定义为一种“粉丝文化”,只是满足原作爱好者的心理需求,而不能像一般作品一样满足一切读者的需求。对“好玩的心理”的强调,也暗含了对“粉丝文化”的定位。这种定位容易导致对角色借用这一文学现象历史性的忽略,从而在法律评价中带入某种偏见。鉴于“同人作品”本身并非法律用语,还可能带来某些误导,本文采用“角色借用”的表述,这是对利用方式的描述,与利用者的身份、动机无关(例如是不是原作的爱好者)。
在角色借用中,有关文学作品角色的争议最大,因为美术等视觉作品中的角色已经形成具体的视觉形象,对此类角色的借用通常表现为具体造型的直接复制,明显地构成表达之再现。而文学角色的借用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使用,则有较大争议。故本文将论题限定为“文学角色的借用”。
在知识产权界的既有讨论中,角色借用通常是在“角色的著作权保护”和“同人创作是否侵犯著作权”两种话语下被涉及,角色借用本身是负面的,问题的重心在于是否及如何保护角色的著作权。然而,角色借用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本文即将介绍的,这一现象甚至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之一。著作权法作为调整创作行为的规范,其适用尺度不能无视艺术规律与创作传统。角色借用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侵权因素被讨论,角色借用的自由问题,应当作为和角色著作权保护并列的问题得到关注。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前提,对文学角色保护的裁判规则就必须谨守一个界限:不能使角色借用全然失去法律空间。在个案中提出的侵权标准,应当使潜在创作者能够推断出角色借用的合法界限。
由于我国法学界对角色借用的文学传统与审美意义关注不够,导致现有的法律评价对角色借用过于苛责,某些裁判规则几乎使角色借用失去了合法的生存空间,故而本文将勉力提示:法律评价不可无视创作规律,著作权保护应当顾及文化多样性。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角色借用在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并总结角色借用之所以成为一种创作手法的审美依据。该部分的考察重点是中国文学史,之所以选择这个视角,一是想打破“角色借用是新兴粉丝文化现象”的误解(史的角度),二是提示不要简单地照搬外国经验(中国的角度)。接下来,本文将以“金庸诉江南”案为例,揭示现有的裁判规则与创作规律之间的冲突。最后,本文将分析在现有的著作权法框架之下,如何实现角色借用自由与著作权保护的平衡。
1 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角色借用
利用经典作品的角色进行接续性创作,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接续之作中也不乏名篇。例如,英国作者罗伯特.戴博德(Robert de Board)所著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是一本通俗心理学名著,该作品中的主要角色都借自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著名童话《柳林风声》。法国当代著名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接续日本名著《源氏物语》,创作了《源氏公子最后的爱情》。在“同人文学”的概念流行之后,我国的文学研究者开始追溯本土的“同人文学”源流。有观点指出,“‘同人小说’、‘同人文学’的称谓虽然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晚,但是此类文学作品其实在我国古代就出现了。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所有的演义、演绎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同人”创作……”[3]引起最多研究的,是清末的“翻新”小说与“同人”创作的关系,[4]有些文章甚至认为晚清的“翻新”小说是“中国网络同人小说的本土文化渊源”。[5]
所谓晚清“翻新”小说,是指清末涌现的一批借用经典而书名中带有“新”字的作品,例如《新三国》、《新西游记》、《新石头记》、《新水浒》、《新金瓶梅》等。这些作品都沿用了原著的角色,但不同于高鹗续《红楼梦》之类的传统续书,而是大胆地转换了原作的时空,例如贾宝玉学外语并全球探险、林黛玉留美之后在日本大学当教授、唐僧师徒来到上海十里洋场闹出种种笑话等,和现在的“同人”创作极其类似。对于这一文学现象,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称之为“拟旧小说”:“晚清又流行着所谓‘拟旧小说’,产量特别的多。大多是袭用旧的书名与人物名,而写新的事。”[6] 1997年,欧阳健教授发表了《晚清“翻新”小说综论》,认为“拟旧小说”之谓不当。他引用了《新水浒》作者西冷冬青的自道——“所以在下要演出一部《新水浒》,将他推翻转来,保全社会”,以及冷血所著《新西游记》的《弁言》——“《新西游记》虽借《西游记》中人名事物以反演,然《西游记》皆虚构,而《新西游记》皆实事,以实事解释虚构,作者实寓祛人迷信之意”,从而提出:“‘翻转’、‘反演’云云,带有翻案、翻新的意思,从尊重作者的创作动因出发,名之曰‘翻新小说’,可能更为贴切。”[7]自此之后,绝大多数文学研究者都沿用了“翻新”的表述,反映出当代文学界更多地肯定了角色借用中包含的创新。
据欧阳健教授的说法,由于阿英在晚清小说研究界具有权威地位,他对“翻新”小说的偏见使得这些作品长期被忽略和漠视,除了个别作品,多数不曾进入阅读和研究的领域。[8]不过,大多数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对角色借用现象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例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在介绍明代前中期文学时,首先注意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并非绝对的原创,书中称:“明代改定小说名著之成就,可谓无与伦比。”[9]之所以说“改定”,是因为这些小说是以之前的民间传说、说书话本为基础的。所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认为:“由于明代的改写,才使得早期的叙述和材料最终成为‘小说’。”[10]在介绍明代戏曲时,《剑桥中国文学史》用了“戏曲的改写与创新”这一标题,指出戏曲发展也和小说类似,是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发展的。例如李开先的《宝剑记》借用了《水浒传》,重写了林冲的故事,把林冲的发配原因改成了多次弹劾奸臣。在清初文学部分,《剑桥中国文学史》有一节标题为“夺胎换骨:评点、续书、传承”,介绍了清初对明代小说的续写现象。当时有些续书的时空转换手法已经非常大胆,如同当下的穿越小说。例如《水浒别传》写梁山英雄及其后裔在暹罗另立基业,并欣赏《水浒传》的演出。《剑桥中国文学史》评价道:“评点与续书都标帜小说文学自觉的高峰。”[11]该书对作者何以续写的历史原因作了同情的解读:“明代小说的清初续书,以模仿、继续、延伸、重写、反驳种种形式出现。《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北宋末年覆亡在即的时代背景,显然可以比附明末清初的离乱。”[12]在介绍续写《红楼梦》现象时,该书指出:“《红楼梦》并不是第一部被不断重写或续写的小说作品。很多小说在十七世纪中期就经历了多次‘转世’,而明清易代更刺激了续书的激增,以此来表达政治对抗、文化反思以及补偿性的乌托邦愿景。”[13]总体上,《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叙事文学中的角色借用和改造现象,是从其历史原因和审美依据上作肯定性评价的。在下卷导言中,编者认为:“中国文学有一个生生不息的特征,那就是现在与过去始终保持着回应与联系。”[14]
齐裕焜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指出,“它(中国古代小说)演变的方式,基本上是同类小说的纵向延伸和不同类型小说的横向融合两种方式。”[15]纵向延伸的方式之一是扩大,扩大的直接方式是续书,“续书多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有现象”[16],扩大的另一种方式是由一人扩大到一个家族,例如由薛仁贵扩大到薛家将。横向融合是指不同类的小说融合后产生新的类别,书中举了《水浒后传》为例,《水浒后传》在英雄传奇中加入了才子佳人,体现了随着时代变化妇女观的转变。[17]不难看出,无论是扩大还是融合,都包含了角色借用。该书多个章节专门介绍了经典名著的续书,对续书的文学价值均作了客观的肯定评价。金庸先生在《书的“续集”》一文中也认为:“随便想一下,旧小说和戏曲中有续书的,实在举不胜举”,并称自己的《书剑恩仇录》出现续书是“合于传统的事”。[18]
2 文学角色借用的美学依据和文化价值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文学角色的借用是古代文学的共性,对此波斯纳在《法律与文学》中有充分的介绍,例如莎士比亚戏剧写作的典型方式是“从一部现存的历史、传记或戏剧作品中借用角色和大多数人物……”[19]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古代没有著作权,所以对在先作品的借用是比较自由的,其次也有商业利益的驱动。但是,如果只有这两点原因,则角色借用与抄袭存在的根基无异,并不值得法律作特别的对待,甚至可以通过法律予以消灭。需要关注的是,除了缺乏权利意识和利益驱动外,角色借用是否具有艺术上的正当性。如果角色借用毫无审美意义,很难解释三个现象:1、在著作权法出现之后,角色借用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当代作家续写、改写《阿Q正传》的小说有二十多部[20];2、很多伟大、严肃的作家也借用在先作品的角色,例如汪曾祺先生的《聊斋新义》;3、角色借用型作品中不乏优秀之作。例如文艺评论家夏济安不喜欢《西游记》原著,却对董说的《西游补》高度评价,认为“董说的成就可以说是清除了中国小说里适当地处理梦境的障碍。中国小说里的梦很少是奇异或者荒谬的,而且容易流于平板。……可以很公平地说:中国的小说从未如此地探讨过梦的本质。”[21]
关于角色借用的审美依据,涉及诸多美学理论,鉴于本文的论域为法学,不宜在美学角度作过多的探讨,仅对角色借用分析中引用最多的两个理论作一点简要介绍。
2.1 接受美学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轨迹大致经历了作者中心论——作品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的演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美学以作者为中心,20世纪初的美学理论偏重文本自身的独立性,20世纪60年代又出现了接受美学,该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既不取决于作者的意图,也不是隐藏在文本中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生成的。”[22]在接受美学看来,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是由作者的创作意图固定的,而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出来的。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泽尔( Wolfgang Iser)认为,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激发、诱导着读者进行创造性填补,这是文学作品的召唤力。[23]如果我们超越作者中心主义,承认文本的独立性和读者的主动性,就能够理解,几乎所有的文本都会存在意义空白和不确定之处——尤其是包含角色的叙事文学,因为有角色就有命运的展开,读者进行创造性填补的冲动会格外强烈。金庸先生发现,“给小说或戏剧写续集,这种兴趣似乎是十分普遍的……既有兴致写作,为什么不另外写一部小说呢?”[24]答案正在于此。越是伟大的作品,文本的意义空白越大,诠释的可能性越多。当具有填补冲动的读者兼有写作能力时,填补的方式就不止于想象,而是可能发展为接续写作。所有的角色借用型创作都要以阅读原作为基础,在阅读中被激发的填补冲动,是常见的创作动机之一。典型的“同人创作”的主体是原著爱好者,恰好验证了接受美学。
例如,在《红楼梦》中,“无才可去补苍天”只是宝玉的一个来历交代,并非重要情节。吴趼人却捕捉到“补天”的另一重可能意涵:建立美好世界,于是他在《新石头记》中让宝玉宣扬民主思想并因此遭到逮捕,后来到达一个军事、政治、科技、道德水平都极高的乌托邦。《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敏锐地指出:“‘天’在此仍然意味着完美世界的唯一象征,但是,它不再是宗教话语中神的恩赐,也并非政治话语中权的象征。‘天’是中国寻求富强的终极期望。”[25]《新石头记》发掘了“补天”意象的新内涵,反映了晚清萌发的对现代化的渴望。借旧之手段,恰恰强化了新变的效果。
2.2 互文理论
互文(intertextuality)一词由法国符号学家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是指“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26]其思想源头是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Bakhtin)的复调理论,克里斯蒂娃把巴赫金的观点表述为:“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27]互文理论对文艺批评的最大影响是,作品不再被孤立地看待,或是仅仅从作品与作者的关系中被审视,而是被置于作品与作品的关系之网中。互文理论对很多文学现象都有解释力,例如引用、戏仿和续写等,这些手法就是要唤起读者过往的阅读记忆,通过一种文本链接的方式达到孤立文本所不具备的效果。通过互文理论,就不难理解何以有些极富创造力的作者要借用在先作品中已有的角色——例如鲁迅著《故事新编》。他们不是怠于创新,而是把互文作为一种创作手法,意图通过与在先文本的链接、对照达到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正如吴泽泉博士对晚清“翻新”小说的评析:“翻新小说对古典小说的改写,首先意在表达对古典小说思想主旨的颠覆。在实际创作中,这种颠覆是通过‘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实现的,即借用旧的古典小说的躯壳与框架,叙述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新的故事在精神主旨上和原作迥不相同,与原作构成一种批判性的互文关系。”[28]
对角色借用持贬斥态度者,通常是因为没有看到借用在艺术上的必要性。阿英就曾质疑:“但问题在于要传达这一切,又何必定要利用旧书名、旧人物呢?”[29]的确,在旧的美学眼光来看,全然原创的作品是最值得赞赏的,续作总难免背负狗尾续貂之恶名。但事实上,原创程度与艺术价值并不等同。正如波斯纳法官所言,“乔叟、莎士比亚以及弥尔顿对继承来的或借用来的主题和材料所做过的事情……同在版权意义上完全原创之文学作品通常达到的高度相比,他们所做的事情体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创造力。”[30]国内有学者提出了独创性与互文性相互倚重的观点,认为“‘独创性’是文学创作的最终目标,的确至关重要,只是它又必须靠‘互文性’来实现,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31]作家张怡微在《小说续书可否看作创意写作》一文中也提出,“小说续书为什么不能看作是中国的创意写作呢?……如果我们将续书的再创作行为,看作对经典文化有意识的补充,是一种次文化生态的表现,那么续书研究的边界将被进一步拓宽。在创意写作学科本土化的过程中,也不必迟迟找不到方向。”[32]
在著作权法中,作品被视为财产,“不借用他人作品”更加符合尊重财产权的价值观,因此原创神圣观念很容易被著作权制度所强化,波斯纳法官斥之为“荒谬的想法”。[33]中国历史悠久、且建立著作权制度的时间很短,恰好为借用自由与创造力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试验场。仅就我国古代小说而言,欠缺知识产权保护固然可能成为“题材相对集中,因袭现象比较严重”的原因之一[34],但另一方面,也使某些精品得以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产生。在我国的四大名著中,至少有三大名著(除红楼梦外)被公认为是集体创作的结果。《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由一个集大成的天才作家最后打磨成精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借用《西游记》角色的《西游补》高度评价,赞之曰:“奇突之处,实足惊人,间以诽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35] 可以说,中国文学史为波斯纳法官的一个判断提供了论据:“扩大对文学作品版权保护,不管是通过制定法或是通过司法解释……这个建议都不能用文学史或文学理论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36]准确地说,所有的古代文学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波斯纳法官是通过考察西方文学史得出上述结论的。这也提示我们,像美国这样历史较短、且建国不久就有了著作权法的国家,在自由借用基础之上产生精品的样本不足,其社会心理可能更偏向重商主义和原创神圣主义,对于借用自由的文化价值未必有足够的认识,我们在进行比较研究时不可盲目照搬其司法经验——像波斯纳这样熟知文学史与美学理论的法官毕竟寥寥。
3 文学角色借用规律与司法裁判的冲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学角色借用有其美学依据与艺术价值,甚至构成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当然,漫长的无著作权期是这一传统形成的制度背景。那么,有了著作权法之后,能否让角色借用变得像抄袭一样彻底为法不容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单纯的角色借用(不包含其他的复制表达的行为)本身是一种创作手法,虽然借旧,意在出新。单纯的角色借用非但不同于抄袭,也不同于改编。改编是以一种新的符号重述原作(例如把文字符号转换为视听符号),是“换着说”,改编之中包含了复制。而角色借用并非要重述原作,是“另外说”。既然演绎创作都有合法空间,创新程度更高的角色借用当然应该被容许。或许有观点认为,角色借用产生的佳作并不多见,为了强化著作权保护,可以牺牲一部分非主流创新,将此作为制度成本。这种看法是违反著作权制度价值目标的。法律无力评价艺术价值,著作权法推动文化进步的机制是通过鼓励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提高佳作产生的概率。因此,著作权法对作品认定的标准(包括独创性判断、作品类型判断等)极其宽容,绝大多数在法律上独创的作品都是平庸之作,精品就在这大量的平庸之作的基础上涌现。如果法律要主动消灭平庸之作,文化就丧失了多样性土壤,精品也难以产生。著作权法对创作的宽容,是其得以鼓励创作的必要品格。有文学研究者指出,“文学经典的改写之作固然鲜有可以与前文本相匹敌的,但是,在‘经典改写’业已成为作家‘创造性叛逆’重要手段的后现代时期,改写之作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价值应给予足够的重视”[37]。任何创作手法——即便是非主流的手法,在法律制度之下都须有存身之处,这应该成为著作权司法的基本价值判断。
因此,是否为角色借用这一创作手法保留了合法可能性,是评判相关司法裁判妥当与否的重要标准。为了确定角色借用的存在空间,首先梳理一下为达到互文效果所必需的最低借用程度:
1、需要借用在先作品的角色名称。只有通过名称,角色借用才得以可能。
2、对名称的借用足以唤起对在先作品的联想。借用必须产生链接的效果,使读者联想到在先作品,对照、反讽等互文效果才能够产生。
3、在先作品通常是经典作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经典作品的角色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文本中的意义空白也较多,最容易激发读者接续创作的冲动。从互文的角度而言,“并不是所有的作品在作家心目中都有改写价值的,它常常是以文学经典文本为对象,是对文学经典的‘再语境化’,是改写者与经典作家的互文游戏。”[38]同时,只有经典作品的角色名称才为公众熟知,可以唤起读者的联想。
遗憾的是,如果依据我国某些司法裁判规则,上述条件很难实现。本文以最著名的“金庸诉江南”案为例,在此案中,被告的角色借用基本控制在以上总结的最低限度:只借用了角色名称,没有复制原告的表达;被告作品的故事与原告作品截然不同,但角色借用足以唤起读者对原告作品的联想,由此产生一种时空穿越的新奇对比效果;被借用的原告作品属于名作。本案的一、二审判决均认定被告构成侵权,兹将两审判决确定的规则总结如下。
一审判决认为被告未侵犯著作权,但构成不正当竞争。认定不正当竞争的两个重要依据是:1、原告作品的知名度。判决认为,“原告对作品中的人物名称、人物关系等元素创作付出了较多心血,这些元素贯穿于原告作品中,从人物名称的搜索结果数量可见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杨治利用这些元素创作新的作品《此间的少年》,借助原告作品整体已经形成的市场号召力与吸引力提高新作的声誉……夺取了本该由原告所享有的商业利益。”[39]2、被告属于营利性使用。判决明确指出,“若‘同人作品’创作仅为满足个人创作愿望或原作读者的需求,不以营利为目的,新作具备新的信息、新的审美和新的洞见,能与原作形成良性互动,亦可作为思想的传播而丰富文化市场。”[40]言外之意,如果被告的借用是非营利性的,则不具有非法性。
如果从该判决推理角色借用的合法空间,应该是:借用非知名作品的角色,且不得营利。这个规则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借用非知名作品的角色难以唤起读者联想,互文效果无从产生,从根本上背离了角色借用的艺术规律。
其次,单纯的角色借用是借旧出新,和原作的欣赏毫无替代关系,“夺取了本该由原告所享有的商业利益”这一判断难以成立。当然,除非法律上认为角色借用应当征得许可,此时可以认为原告应得许可费而未得,但这一结论是不成立的,后文将对此进行论述。如果原告的商业利益受损无法证成,则没有理由要求被告作品的传播是非营利的。被告的营利影响了原告的营利,“非营利”之约束才有正当性。
再次,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考量,如果某种创作手法是应当被容许的,则法律也应该容许该创作结果的传播。在当代社会,非营利性的传播渠道是极其有限的,尤其在网络环境下,即使是免费网络传播,也可能带来流量收益,除非作者自己赔钱复印发送才是安全的。所以,“非营利”的限定很容易让角色借用者动辄得咎。
二审判决确认被告没有利用原告的作品情节,但依然判定被告侵犯了著作权,理由是:“《此间的少年》中出现的绝大多数人物名称来自查良镛涉案四部小说,且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物关系、人物背景都有较多相似之处。虽然就单个人物形象来说,难以都认定获得了充分而独特的描述,但整体而言,郭靖、黄蓉、乔峰、令狐冲等60多个人物组成的人物群像,无论是在角色的名称、性格特征、人物关系、人物背景都体现了查良镛的选择、安排,可以认定为已经充分描述、足够具体到形成一个内部各元素存在强烈逻辑联系的结构,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41] 也就是说,多个角色名称、性格特征、人物关系和人物背景构成表达,对多个角色的借用构成对表达的利用。判决也注意到法律与文学实践的互动关系,指出“而对文学创作来说,模仿与借鉴历来是常用手段……故对于文学作品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并不能一概而论适用停止侵害……”[42]
从该判决推理出的角色借用的存在空间是:1、可以借用单个角色,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单个人物形象往往被认为难以构成表达本身而得不到著作权法的保护。”[43] 2、有可能不必停止侵害。该规则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利用在先作品的角色名称,就是要借用在先的角色设定,因此必然要延用原作中的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和人物背景。否则,借用名称就失去了意义。原被告作品中同名的人物却毫无联系,如何产生互文效果呢?人物关系是人与人之间产生的,所以角色借用通常都会借用多个,只借用单个角色的情形极其罕见。如果非法性是源自“借用过多”,那么借用几个角色就是合法的呢?判决论证“单个角色不受保护时”认为,“(读者)对人物所形成的具体认知与情感亦有差别,因而最终在读者脑海中所形成的人物角色形象也各不相同。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44]这个论证应该与角色的数量无关,不会因为量变发生质变。
其次,如果单纯的角色借用是侵犯著作权,就会存在停止使用的风险,虽然在个案中法官作了缓和的处理,但潜在角色借用者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形成预期,很可能会被迫放弃这种创作手法。
综上所述,“金庸诉江南”案的裁判规则基本上否决了角色借用的自由空间,有文章因此表达了悲观的看法:“‘金庸诉江南案’之后中国将再无同人作品。”[45]理论上,角色借用还有一种合法可能性:借用者事先征得许可。这一方案成立的前提是,角色借用构成了对表达的利用,否则许可的基础不存在。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第四部分讨论。现在仅从创作规律的角度质疑这一方案。如前所述,单纯的角色借用不同于改编,改编是用新的语言重述作品,易于得到原作者的许可,而角色借用是“旧瓶装新酒”,甚至可能包含对原作批判、反讽的动机,续作不合原作者心意的概率较高,很难获得许可。著作权法之所以把“为评论而引用”列为合理使用,重要考量之一,就是避免原作者借许可之机对评论进行言论审查[46]。单纯角色借用需要原作者许可,不符合宽容此类创作的初心——保护文化多样性。
毫无疑问,我们要尊重已经建立的著作权制度,对角色借用的宽容不能只停留在价值判断,还要在现有理论与规则的框架内找到依据。前文已经分析了文学角色借用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借角色之名;借用程度与所借作品的知名度足以唤起公众联想、以产生互文效果。下文将这种借用称为“最低限度文学角色借用”,并检验其在现行法之下是否具有合法性。
4 最低限度文学角色借用的合法性
最低限度的文学角色借用直接表现为借用了角色名称,由于原作已经为角色设定了身份,经由名称,通常会唤起读者对原作中角色设定的联想,例如角色之间的关系。脱离具体情节的角色名称和角色设定是思想还是表达,往往是争议的焦点。当然,脱离个案,很难一般性地描述思想与表达的界限,但可以肯定的是,二分法的主要规范意义,是为了合理地确定保护范围,避免财产权的范围过大。思想是抽象的,抽象则无边界,在抽象之上可以形成无限的具体,而财产权的范围必须是有限的。西方学者对“idea(思想)”和“expression(表达)”的区分,一般都以是否“具化”为标准。[47]如果利用的元素远不足以把作品特定化,在理论上有无限的具化可能,则不宜认定为表达。假如作品A可以明确地指向B,A与B很可能构成实质相似。反之,如果作品A与B的相似程度可能同时指向大量的作品,则通常被认定为思想相似,否则A之上的财产权可能控制大量的作品。假设一个作家在写作之前列了个大纲,选好了数个人物名称,想好了人物的身份与关系,充其量只能认为该作家形成了创意,不能认为该作家已经形成了小说的表达,因为这几个人物设定可以形成无限的表达。同理,在小说完成之后,仅仅从小说中借用了角色名称并沿用了原作的身份与关系设定,也应当认定为只是利用了思想。在一些认定“角色借用属于表达利用”的判决和论文中,有一个明显的说理缺陷:只论证角色是表达的一部分,而没有论证借用行为本身的性质。在“金庸诉江南”案中,二审判决认为,“只有当人物形象的各要素在作品情节展开过程中获得充分而独特的描述,并由此成为作品故事内容本身时……才有可能获得著作权法保护。”[48]这段话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表达是一个整体,由很多元素构成,不可能存在无角色的故事,保护小说的表达,当然就包含了对角色描述的保护。但是,判决并没有分析被告借用的行为性质。一个元素在作品中构成表达的成分,无法推出“从原作中抽离该元素也一定构成表达的利用”。例如,作品的标题是表达的组成,但单独利用标题未必侵犯著作权。判决已经认定被告没有“提及、重述或以其他方式利用”原作情节[49],那么,角色名称及其身份设定一旦从原作情节中抽离出来,如何能够构成“故事内容本身”呢?有观点认为,“研究者或裁判者不应脱离该角色存在于其中的作品去判断角色是否构成表达或仅属抽象的思想”。[50]同理,在判断侵权时也不能脱离角色与原作的关系,换言之,不能无视“原作中的角色”和“脱离原作的角色”之间的重大差异。从表述上看,二审判决有可能受到美国判例所谓“角色构成故事”标准的影响。如前所述,在处理角色借用自由与著作权保护的关系方面,美国经验未必是一个好的样板,没有必要偏离“思想-表达二分法”这样成熟的一般性规则,轻率地去采纳域外法院在个案中提出的非普适性具体规则。
“金庸诉江南”案二审判决已经认识到,能够获得著作权保护的,是关于角色的“充分而独特的描述”。该案被告既没有复制文句,又没有再现情节,根本不存在对“描述”的利用,但判决却认为侵犯了著作权。类似的问题在“《楚留香传奇》”案一审判决中也存在,判决一面认为“《楚留香传奇》在描述上述故事情节中的具体人物安排、故事发展线索、人物性格的体现等具体内容,可以构成表达”,同时确认被告的作品没有利用情节(即没有利用“描述”),最后又认定被告侵犯著作权。[51]造成这一推理缺陷的原因是,文学角色的借用常常会引发一种错觉:把唤起联想误认为复制。由于原作已经完成,角色的相同会使读者形成想象性链接,把原作的设计与续作的表达拼接在一起,这正是角色借用意欲达到的互文效果。但是,唤起联想并不等于复制。复制是一种客观行为,是否复制、复制了多少,都是客观的。在侵权案件中,复制的量会影响损害赔偿的计算。而读者是否发生联想、联想了多少,是完全不确定的。如果读者未阅读过原作,联想甚至无从发生。因此,唤起联想在不正当竞争认定中有法律意义(例如可能引起混淆),在侵犯著作权认定中没有法律意义。最低限度的文学角色借用不包含语句与情节的复制,根本不存在对原作表达的再现,从而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使用。
关于唤起联想与复制的区别,还可以通过比较角色借用与抄袭来理解。抄袭者会刻意改掉原作的角色名称,但即便如此,一般读者还是会感受到原作与抄袭之作的特定联系,说明表达之间构成了实质相似。而在角色借用的情形下,如果把角色的名字全部换掉,读者通常不能发现原作与借用之作的联系。这充分表明,借用的对象只是角色名称,是名称提示了读者,从而产生联想。而为了达到互文效果,角色名称是必须借用的。
既然最低限度的文学角色借用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利用,原作著作权人要求借用者事先获得许可,也就缺乏权利基础,因此从法理上回答了本文第三部分提出的“原作著作权人有无潜在许可费损失”的问题。
当然,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依然有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例如有意引起市场混淆,使读者误认为是原作者自己的续作。但要注意的是,基于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原作的知名度、读者对原作的联想和被告行为的营利性这三个因素本身不足以证明行为的非正当性。如果借用者不复制语句与情节,仅仅是唤起读者的联想,恰恰说明借用者是诚信的,把借用尺度控制在互文效果所需的必要范围。
5 结语
借用有一定知名度的在先作品的角色名称,唤起公众对原作的联想,但无须复制原作的情节,即可满足角色借用所追求的互文效果。这种最低限度的文学角色借用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实质性利用。被借用作品的知名度和读者的联想唤起,是互文效果的必要条件,不具有非法性。最低限度的文学角色借用意在借旧求新,与原作没有竞争关系,不会损害原作的市场。既然角色借用未利用表达,原作著作权人的许可缺乏权利基础,也不存在原作潜在许可市场的损失。因此,角色借用的营利性本身也不具有非法性。
综上,最低限度的文学角色借用既不侵犯著作权,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如果角色借用超过最低限度,有可能构成侵权,但也不排除合理使用的可能性,需要个案检验。在处理文学角色借用纠纷时,妥当运用现有法律理论与规则,完全可以兼顾文化多样性与著作权保护。
注释
[1]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2068号民事判决书。
[2] 同注1。
[3] 刘东方:《“同人”与“翻新”——论当下同人小说与近代翻新小说的承继关系》,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4] 参见吕琼峰:《未著录的《贾宝玉秘记》———兼论晚清“翻新小说”对“同人小说”的影响》,载《明清小说研究》2020年第2期。
[5] 刘小源:《被遗忘的晚清反案小说:中国网络同人小说的本土文化渊源》,载《百家评论》2019年第1期。
[6] 阿英:《晚清小说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7] 欧阳健:《晚清“翻新小说”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5期。
[8] 同注7。
[9]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0页。
[10] 同注9,第71页。
[11]同注9, 第242页。
[12] 同注11。
[13] 同注9,第376页。
[14] 同注9,第19页。
[15] 齐裕焜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0页。
[16] 同注15,第10页。
[17] 同注16。
[18] 金庸:《书的“续集”》,载《寻他千百度》,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46页。
[19] 【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与文学》(增订版),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8页。
[20] 古大勇:《论当代作家对<阿Q正传>的续写与重写》,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9期。
[21] 转引自张怡微:《小说续书可否看作创意写作》,载《上海文汇报》2019年9月4日第11版。
[22] 任卫东:《西方文论关键词:接受美学》,载《外国文学》2022年第4期。
[23] 参见丁莉:《<源氏公子最后的爱情>——东方文学经典在西方如何被续写?》,载《外国文学》2022年第6期。
[24] 同注18,第43页。
[25] 同注9,第505页。
[26] 【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7] 同注26,第4页。
[28] 吴泽泉:《暧昧的现代性追求——晚清翻新小说论纲》,载《济宁学院学报》2011年第32卷第1期。
[29] 同注6,第180页。
[30] 同注19,第539页。
[31] 李桂奎:《中国古典小说互文性研究》,第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32] 同注21。
[33] 【美】理查德.波斯纳:《论剽窃》,沈明译,第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4] 同注15,第6页。
[3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36] 同注19,第549页。
[37]李玉平: 《互文性: 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 216 页。
[38] 李明彦:《20世纪中国小说互文改写的三种类型》,载《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39] 同注1。
[40] 同注1。
[41]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8)粤73民终3169号民事判决书。
[42] 同注41。
[43] 同注41。
[44] 同注41。
[45] 金水:《“金庸诉江南案”之后中国将再无同人作品》,载《经济观察报》2023年5月22日第8版。
[46] 【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47] 参见李琛:《著作权基本理论批判》,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48] 同注41。
[49] 同注41。
[50] 刘银良:《文学角色的版权保护:以“金庸诉江南案”为例》,载《中国版权》2024年第1期。
[51]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2)京73民初435号民事判决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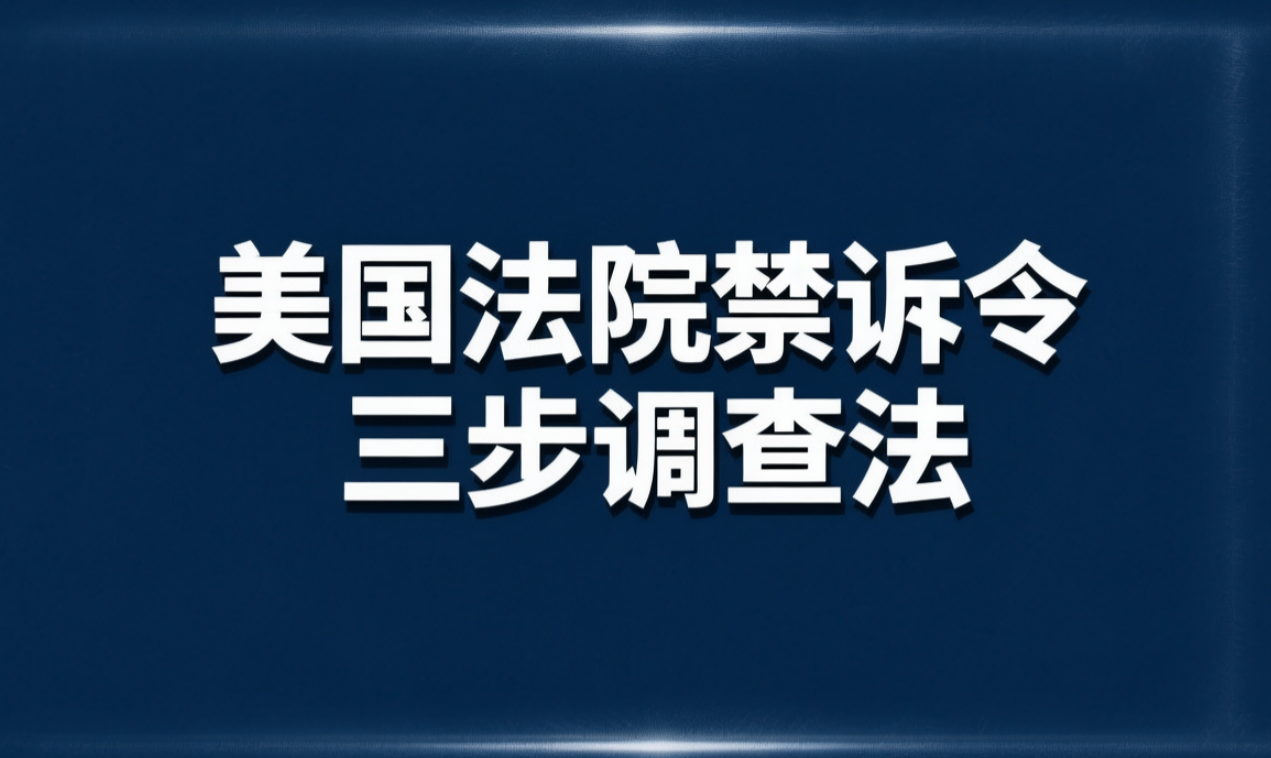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上一篇
上一篇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