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利
专利 -
 商标
商标 -
 版权
版权 -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
 反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 -
 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 -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 -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律师动态
更多 >>知产速递
更多 >>审判动态
更多 >>案例聚焦
更多 >>法官视点
更多 >>裁判文书
更多 >>“SΛMSUNG”是三星电子株式会社在中国已获准注册的有效商标,三星电子株式会社特别授权其在中国投资设立的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三星中国公司”)负责“SΛMSUNG”商标的使用、管理和保护。被告人郭明升,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6月的七八个月时间内,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未经三星中国公司授权许可的情况下,伙同被告人孙淑标、郭明锋,从他人处批发假冒款型为I8552的三星手机裸机及其配件进行了组装,利用其开设的“三星数码专柜”淘宝网店开展了“正品行货”宣传,并公开对外销售标有“SΛMSUNG”商标的手机,且其销售价格明显低于真品三星同款手机的市场价格。经查,该网店组装并销售或组装假冒I8552款型三星手机共计20000余部,非法经营数额多达2000余万元,非法获利多达200余万元。该案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6日发布的郭明升、郭明锋、孙淑标假冒注册商标案(以下称“郭明升等假冒注册商标案”),即指导案例87号(第16批指导案例之一),也是目前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唯一一例商标类犯罪判例。该案由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8日作出(2015)宿中知刑初字第0004号刑事判决书,一审宣判后,郭明升等三被告人均没有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该案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和非法经营数额等关键问题,从我国大量司法实践的视角再重新考察假冒注册商标罪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一、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且“情节严重”,就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所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罪。可见,只有侵犯注册商标权才可能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而侵犯未注册商标权的,则不可能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更为重要的是,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还有“同一种商品”和“相同的商标”的标准要求。
(一)“同一种商品”的事实认定
就“同一种商品”的含义而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1〕 3号)(以下称“《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意见》”)第五条规定,其是指“名称相同的商品”或者“名称不同但指同一事物的商品”。本条所指的“名称”是《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规定的商品名称,亦即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布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所规定的商品名称,这是由于此区分表是根据《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制定的,目前最新版本为2019年发布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基于尼斯分类第十一版(2019年文本)》。这里的“名称不同但指同一事物的商品”具体是指“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通常以为其属于“同一种事物”的商品。这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所规定的“类似商品”基本相同。该区分表开宗明义地规定,类似商品是指商品的“功能、用途、所用原料、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存在某种共同,如若使用在相同或近似商标上,可能会使相关公众视为它们之间具有“特定联系”,进而易于使相关消费者误以为其同属一家企业制造的商品。[1]两者在考虑因素或判断标准上均采用了“主客观统一说”标准,没有采用单一的“客观说”标准,也没有采用单一的“主观说”标准。[2]概言之,司法解释对“同一种商品”进行了扩大解释,扩展至“类似商品”。[3]
不过,《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意见》第五条还强调:判定“同一种商品”,应当将“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结合“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进行比对,进行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例如,在东莞市格雷诺电气有限公司、东莞市铂尔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等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中,法院从功能或作用方面将施某电气公司(SCHNEIDER ELECTRIC SE)第G715396号“图片”商标在第9类商品上核定使用的“用于电的运输、处理、开关、转换、积累、调节、过滤、测量、信号、检测或控制的科学、电气、电子装置和仪器,包括上述器材的电气、电子元件,整流器,半导体、继电器(电),电容器,断流器,断路器,电开关,接触器,自动机,控制板,静态转换器,程序控制器,计算机,计算机用电源系统,计算机用安全微系统,断路保护电源,换流器,电池组,蓄电池”和被告实际生产的“SM6系列环网柜(开关柜)”视为同一种商品。[4]在陈洪生、江苏华都电气有限公司等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中,法院将西门子股份公司(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第G637074号“SIEMENS”商标在第9类商品上核定使用的“高压、中压、低压成套设备与连接器”与陈洪生、江苏华都电气有限公司等被告人实际生产的“母线槽”视为同一种商品。[5]在郭明升等假冒注册商标案中,法院也将三星电子株式会社第3038519号“SΛMSUNG”号商标、第694540号“S Λ MSUNG”商标、第2021773 号“SΛMSUNG”商标等核定使用的“移动电话”“便携式通讯设备”“电话装置”等商品与郭明升等三被告实际生产的“手机”视为同一种商品。总之,司法实践中对“同一种商品”的认定偏宽,已扩大到了“类似商品”。
(二)“相同的商标”的事实认定
就“相同的商标”事实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以下称“《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其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为侵权商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第二种情形为侵权商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视觉上基本无差别”且“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即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相同”。这里的“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即指很可能造成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或者易于使相关公众产生行为人与商标注册人之间具有某种特殊关联性的错误认识等情形。[6]《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意见》第六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了“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即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相同”)的四种具体类型:与该注册商标相比,侵权商标仅仅改动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或“文字横竖排列”等“细微差别”;侵权商标仅仅改动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间距,但没有影响到注册商标的整体“显著”部分;侵权商标只是改变注册商标的“颜色”;以及其他类似情形的商标。《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也规定:商标相同是指两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使用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7]可见,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对“相同的商标”解释基本一致,都强调了“视觉上基本无差别”和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误认”,其包括“完全相同的商标”和“基本相同的商标”两类。在判断“基本相同的商标”时还要特别考虑以下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要实现刑法保护注册商标权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第二个因素是要控制好刑法调整范围与民法调整范围之间的边界与衔接。[8]但“相同的商标”与“近似商标”的含义悬殊很大。“近似商标”通常是指商标在“字形、读音、含义”(文字商标)、“构图、着色、外观”(图形商标)、“整体排列组合方式和外观”(文字和图形组合商标)、“颜色或者颜色组合”(颜色商标)、“形状和外观”(三维标志即立体商标)、“听觉感知或整体音乐形象”(声音商标)等方面与已注册商标或在先使用权商标近似,若两者使用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则易于造成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混淆。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似的商标”,仅属于一般违法行为,而不能按刑罚论处。[9]
在董浩假冒注册商标罪等案中,被告人在实际生产的背包上使用的商标与保罗弗兰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PAUL FRANK INDUSTRIES LLC)在其核定第18类“包”等商品上使用的“大嘴猴”注册商标完全相同。[10]在杜聪斌、杜阳阳与杜建成、王若飞等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中,被告人在其实际生产、销售的酒上使用的商标与商标注册所有人在其核定第33类“酒”等商品在使用的“蒙古王”“河套王”“草原王”“剑南春”“洋河”“汾酒”等注册商标完全相同。[11]在郭明升等假冒注册商标案中,也遵循了“相同的商标”的法律规定。
可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都严格坚持了相同商标的标准,仅允许字形、排版或颜色上的细微差异,仅包括完全相同商标和基本相同商标,尽量不扩大到“近似商标”。[12]
还需说明的是,在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仅限于对商品商标的保护,没有扩大到服务商标;对服务商标的保护只能通过非刑法的手段加以保护。[13]
二、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
知识产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通过犯罪数额来体现,[14]犯罪数额成为体现知识产权犯罪本质的最明显、最普遍特征,[15]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与量刑,[16]由此对非法经营数额进行认定非常重要。“非法经营数额”是假冒注册商标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要件的具体化和定型化。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主要涉及非法经营数额与违法所得数额的区别、非法经营数额的范围以及非法经营数额的计算等三个核心问题。
(一)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的界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10〕23号)(以下称“《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规定(二)》”)第六十九条规定,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所需“情节严重”的考虑要素主要是“非法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司法解释增加“违法所得数额”这一标准,主要是基于一些案件的非法经营数额查实难度大,但可以查得到违法所得数额。[17]这里的“非法经营数额”,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解释》首先采用的一个概念,这是因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集中体现在侵权的量, 而侵权的量又集中表现为相应的非法经营数额。[18]《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所谓“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相关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过程中所涉侵权产品的总数额,即制造、销售、储存或运输侵权产品的总价值。为造假卖假所支出的机器设备、房租与造假人员工资等投入不属于“非法经营数额”。[19]显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解释》对“非法经营数额”的界定采用了“价值说”,这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支持。[20]
关于何谓“违法所得数额”,《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解释》没有明确规定,这是因为当时讨论时没有形成共识。[21]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批复》(法复〔1995〕3号)(以下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认定“违法所得数额”司法批复》”)解释道:“违法所得数额”,是指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获利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30号)(以下称“《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7条第2款也规定,“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获利数额”。这两个司法解释文件对“违法所得数额”的解释显然都采取了“获利说”,而非“收入说”。2008年11月21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总局令第37号)第三条也规定:违法所得就是“全部收入”减去“合理支出”,所谓“全部收入”是指当事人在违法生产、销售商品中所获取的所有非法收益,所谓“合理支出”是指当事人用于经营活动所投入的一定直接合理成本。这里实际上也采用了“非法获利数额说”。[22]因此,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违法所得数额”可以解释为行为人生产或销售附有或加贴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侵权产品所得的全部非法获利数额,[23]其至少应包括在实施知识产权犯罪过程中获得的已得或应得的销售收入以及加工费、运输费、保管费等,而不应包括行为人实施犯罪的非直接投入(即非直接投入费用应从违法所得数额中扣减)。[24]
由此可见,“非法经营数额”通常会大于“违法所得数额”。这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规定(二)》第六十九条和《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也是吻合的。司法实践中,采用“非法经营数额”标准认定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案件居多,而采用“违法所得数额”标准认定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案件偏少;[25]郭明升等假冒注册商标案也采用了“非法经营数额”标准,而没有采用“违法所得数额”标准。这很可能是因为违法所得要扣除各项费用,计算起来十分复杂,证据收集也很困难。[26]
还需说明的是,单位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与个人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标准是一样的。
(二)非法经营数额的范围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解释》第十二条和《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意见》第7条规定,“非法经营数额”亦即行为人在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中所涉假冒注册商标产品的总数额,既含“制造”“销售”侵权产品,也包括“储存”“运输”侵权产品;既包括“已销售的侵权产品”,也包括“未销售的侵权产品”;既包括已“附着(含加贴)”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侵权成品,也包括还没有“附着(含加贴)”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侵权半成品、原料等,亦即,假冒注册商标标识“已经制作完成”,但其部分或全部没有附着于或加贴于侵权产品的半成品或原材料等;还包括“多次”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的侵权产品行为但“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罚”的侵权产品数额。这里的“多次”是指“二年内”多次实施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的侵权产品行为,但“未经行政处理”,且“累计数额”构成犯罪的,或者“五年或十年内”多次实施前述违法行为,但未经“刑事处罚”,且累计数额构成犯罪的。在胡文朝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中,法院还认为,“加工”侵权产品也属于“非法经营数额”范围。[27]在郭明升等假冒注册商标案中,法院还认为,“组装”侵权产品也属于“非法经营数额”范围。
(三)非法经营数额的计算
对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就是对侵权产品价值的认定。[28]在计算“非法经营数额”时,如果侵权产品已经销售,就依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其价值;如果侵权产品处于制造、储存、运输或未销售的状态,则依照这些侵权产品的“标价”或依照已经查清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其价值;如果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其实际销售价格“无法查清”,则依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其价值;如果假冒注册商标标识“已经制作完毕”但其“尚未附着(含加贴)”于侵权产品,即仍处于半成品、原材料等的状态,且有充实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半成品、原材料等即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则这些侵权产品的价值也要“计入”非法经营数额;而对于多次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但其“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罚”的侵权产品,其非法经营数额应当“累计”进行计算。
问题是,对于标价与实际销售价格均无法确定而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侵权产品价值的方法,实施中存在罪刑不相适应与处罚真空等司法不公问题。[29]在傅波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中,法院认可了“公安机关在无法查清仿冒商品的实际销售价格后,依法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单位进行价格认定”。[30]在胡文朝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中,对既没有标价,也尚未售出,且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的假冒注册商标产品,法院也认可了第三方对假冒注册商标产品的评估价值。[31]可见,在司法实务中,对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法院更多地采用了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的方法。
在郝喜元、武法顺等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中,法院认可了公安机关对已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产品的价值委托会计事务所进行的评估与审计。[32]在菅素兰、马某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中,也采用了中立的第三方对假冒注册商标的已销售侵权商品价值进行评估的方法。[33]在卢科甲、李论等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中,法院采信了第三方对假冒注册商标的已销售产品的价值鉴定。[34]在潘德心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中,法院也采信了第三方对已销售侵权产品价值的鉴定。[35]在张某某等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中,法院认可了第三方对假冒“南德”“太太乐”“莲花”等注册商标的已销售侵权产品的价格鉴定。[36]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不仅对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侵权产品价值,而且对已销售的侵权产品价值,均可采用第三方进行价值评估或审计的方法。
三、结论
不论从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看,还是从司法实践看,对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的商标”的认定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对假冒注册商标罪中“同一种商品”的认定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均已扩大到了“类似商品”。从司法实践看,不仅“生产”“销售”“储存”和“运输”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非法经营”行为,而“加工”行为和“组装”行为也视为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非法经营”行为。司法实践中,不仅对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侵权产品的价值,采用委托第三方评估的方法加以确定,而且对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也采用委托第三方加以评估、鉴定或审计的方法加以确定。
注 释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基于尼斯分类第十一版(2019)》知识产权出版社。
[2] 张泗汉:《假冒商标犯罪的若干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7期, 第31-35页。
[3] 赵秉志、许成磊:《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问题研 究》,《法律科学》,2002年第3期,第67-69页。
[4]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2刑终459号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刑申81号 驳回申诉通知书。
[5]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刑终98号刑事裁定书。
[6] 胡云腾、刘科:《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研 究》, 《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第134-140页。
[7] 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 《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2016年,第63-65页。
[8] 肖晚祥:《假冒注册商标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6期,第 79页。
[9] 黄丽勤、周铭川:《假冒注册商标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研究》,《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第78-79页。
[10]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刑终348号刑事判决书。
[11]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内刑终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12] 同注[2]。
[13] 申夫、王良顺、卢静:《冒注册商标罪新探》,《法商研究》,1997年第2期,第67页。
[14] 同注[6]。
[15] 刘宪权:《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认定分析》,《法学》,2005第6期,第36页。
[16] 王敏敏、兰波:《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数额认定》,《中国检察官》,2012第9期,第19页。
[17] 同注[6]。
[18] 同注[15],第39页。
[19] 胡充寒:《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类型与认定》, 《知识产权》,2014年第9期,第32-34页。
[20] 同注[9]和[18]。
[21] 同注[6]。
[22] 刘丽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2期,第136页。
[23] 同注[2]和[3]。
[24] 同注[6]。
[25]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刑终234号刑事裁定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刑终97号刑事裁定书;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刑终152号刑事裁定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刑终142号刑事裁定书;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2015)豫法知刑终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豫法知刑终字第00003号刑事判决书;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法知刑终字第00002号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刑申13号驳回申诉通知 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刑申14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刑终32号刑事裁定书。
[26] 刘惠、王拓、邱志英、吕晓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探析》,《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5期,第42- 43页。
[27]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刑申3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
[28] 同注[18]。
[29] 同注[26]。
[30]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刑申264号驳回申诉通知书。
[31] 同注[27]。
[32]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豫法知刑终字第00008号刑事裁定书。
[33]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法知刑终字第01号刑事裁定书。
[34]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黔高知刑终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
[35]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刑申193号驳回申诉通知书。
[36]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知刑终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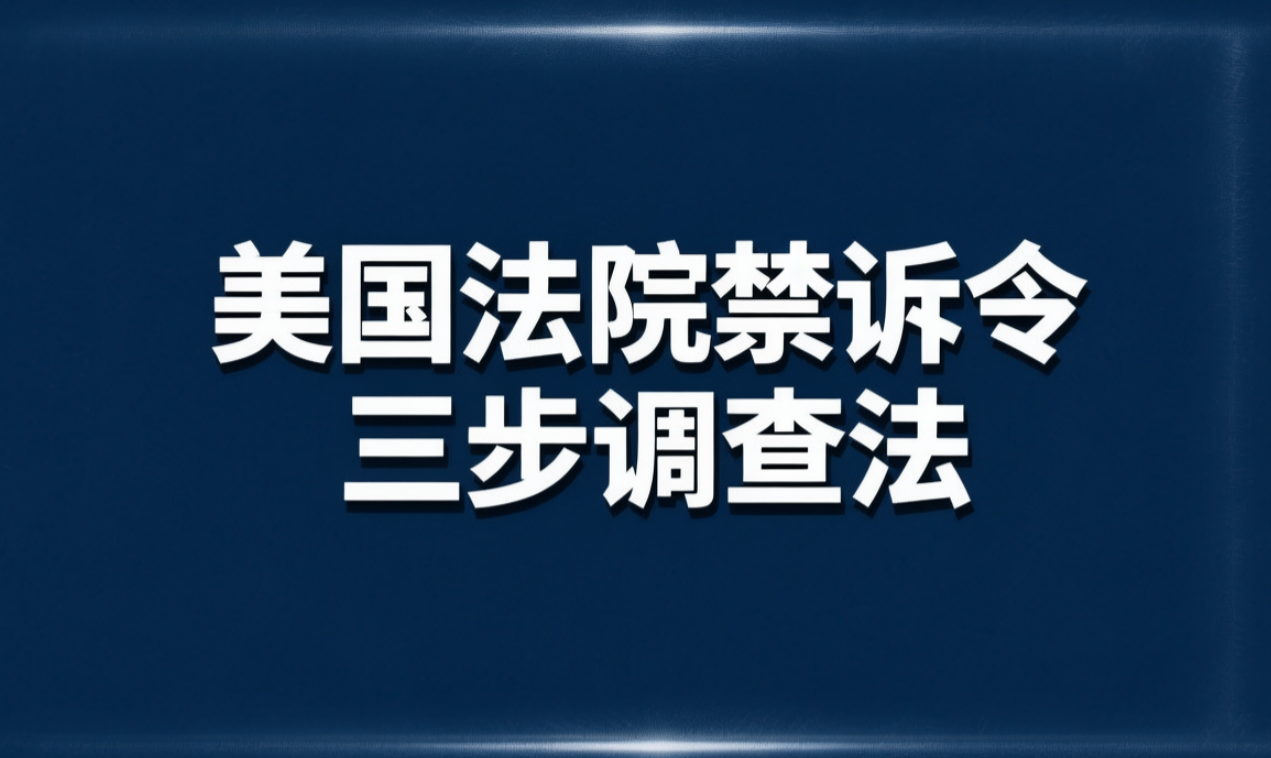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上一篇
上一篇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