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利
专利 -
 商标
商标 -
 版权
版权 -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
 反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 -
 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 -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 -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律师动态
更多 >>知产速递
更多 >>审判动态
更多 >>案例聚焦
更多 >>法官视点
更多 >>裁判文书
更多 >>目前,在我国法律中关于数据权益保护的规则大多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条文中。在司法实践中则是通过数据的类型化识别,在现行的制度体系内探索适应性保护路径。本文拟结合知识产权审判实践,探索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径,以期为处于探索中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助益。
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困境
由于数据要素与传统知识产权之间存在属性差别,在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内,数据权益保护救济,也存在一定的困境。
第一,在理论上,数据的非排他性与知识产权制度以独创性、排他性为核心的赋权逻辑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如何界定权利边界、协调多方利益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国家层面的数据产权立法尚未出台,目前尚无一体化保护规则。
第二,数据的技术特性特征使其与知识产权制度的适配具有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面对数据生产链条的复杂性,传统的确权规则有时难以完全匹配适用,数据产品及匿名化处理的数据为证明权属常需海量举证,司法采纳标准目前尚未完全统一。
第三,权属分配难题使得单一赋权模式难以为继。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主体特定、成果静态呈现的赋权逻辑,“全有或全无”的权属分配模式有时无法完全覆盖数据保护。目前,全国17个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地区都在通过陆续出台数据登记管理的有关办法,探索权利分层架构,以进一步厘清数据流通过程中不同主体的权利边界。但是,对于如何构建数据要素的收益分配机制,尚未形成普遍共识。确权规则的模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据的流通,技术创新的快速迭代与立法滞后性等问题,亟待构建兼顾权属明晰与利益平衡的数据保护协同机制。
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进路
面对数据权属模糊、技术规则复杂与法律适用冲突等核心困境,我国通过“立法审慎探索—司法规则创新—技术工具赋能”的协同路径,逐步构建起适配数字经济特征的司法保护模式。
(一)立法维度:分层分类保护的场景化构建
数据权益的复杂性使得统一的保护模式难以满足其需求,基于生成场景、主体关系及技术特性的差异,可采取与之适配的复合方式,构建“场景化分层”的数据保护模式。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民法典》等,能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可以通过法律适用及司法解释等方式,灵活应对数据领域的新问题。例如,通过法律适用及司法解释,建立分层保护体系,深挖多元制度的协同潜能。同时,也要避免规范冲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中提出,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要探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推进实施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推动建立企业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建立健全个人信息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各参与方合法权益保护制度。目前,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地区都在探索数据确权与保护机制,可待试点地区就数据权益保护在形成稳定经验的基础上再进行成果转化。
(二)司法维度:结合司法实践进行全面保护
司法裁判在数据确权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可探索从全国审结的数据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中,提炼具有指导意义的裁判要旨,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总结归纳数据保护的路径。从已有的裁判样本来看,在实务中各地法院多采取“问题导向、分类适配”的司法模式构建场景化保护规则,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裁判范式:
第一,在著作权方面,数据的选择与编排体现了独创性智力劳动,具备独创性编排结构的数据库,在实践中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汇编作品”范畴。例如,在山东济南某信息公司与某软件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中,济南某信息公司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商标公告资料汇编了一个商标信息数据库,并开发了查询软件,有偿供用户查询并对外销售查询系统。基于此,其主张某软件公司未经许可复制其数据库的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而某软件公司则认为数据来源于公共领域,并非济南某信息公司独创。法院经审理认为,济南某信息公司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的商标公告中的商标信息进行了提取、分类、整理,并加入自定义字段信息,其编排和整理体现出独创性,涉案数据库构成汇编作品。该案裁判中明确了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的独创性认定标准,并强调了在数据编排和整理中体现独创性的重要性。
第二,商业秘密规则的特殊覆盖。涉及核心算法参数、客户画像模型等非公开数据,可参考《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的有关规定主张商业秘密保护。例如,在广东深圳某信息公司诉某智能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以模型的选择和优化作为核心的算法,即便所采用的模型均为公知信息,但若模型的选择与权重排序需通过大数据的收集、处理和测试等,则该算法应视为不为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的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且能为权利人带来商业利益并保持竞争优势,应当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但在实践中,由于技术黑箱、举证难度高,事实上商业秘密规则能够为数据提供的保护程度较为有限。
第三,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的技术化适用。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的裁判逻辑关注的是数据使用行为对竞争秩序的破坏,对于无法满足独创性的数据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兜底保护。例如,在“谷米诉元光案”中,法院首次明确即便数据本身不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但通过技术手段和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形成的数据资源仍属于企业核心竞争资源,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新浪微博诉脉脉案”中,确立了互联网行业中OpenAPI开发合作模式下数据获取的“三重授权原则”,即数据提供方取得用户的同意,第三方平台在使用用户信息时还应当明确告知用户其使用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再次取得用户的同意。“大众点评诉百度案”中则明确了数据使用的“实质性替代”标准,平台对数据资源投入劳动和成本,享有竞争性权益,未经许可的实质性替代使用行为,损害公平竞争秩序,构成反不正当竞争。在司法裁判中已经达成普遍共识,认为经营者对合法汇集、加工或转化的数据资源,投入了采集、加工、运营等成本,该数据资源能够为经营者带来现实或潜在的经济价值的,经营者对数据享有合法权益,未经许可的实质性抓取或者通过合法技术手段获取后实质性替代等,都可能因为破坏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各地法院通过“场景—行为—责任”的匹配,识别数据类型,区分不同的法律关系,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寻求对数据的最佳保护路径。著作权法对具备独创性的数据库赋予数据加工者对抗未经授权的复制行为,商业秘密规则对未公开数据提供分层保障,而不正当竞争通过行为规制为破坏市场秩序行为提供兜底保护。依托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提供的司法救济途径,可以激励数据要素市场的创新与成本投入,同时回应数据交易过程中的保护需求。
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建构
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司法探索虽为数据权益保护奠定了规范基础,但因技术的快速迭代,加剧了数据治理问题的复杂性,数据要素的动态性与技术黑箱效应引发新的治理难题,权属认定标准模糊、损害赔偿量化困难、技术事实查明障碍等困境仍制约着制度效能。鉴于此,需进一步构建“规则统一—个案衡平”的治理规则,即通过构建统一的权利认定标准,在裁判中适用可量化的司法标准,借动态举证规则实现实质正义,从而弥合数据治理的结构性断层,为司法裁判注入确定性基因。
第一,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权利认定标准。基于不同维度的认知,数据权利认定标准存在差异。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欧盟数据库指令》的“实质性投资+商业价值”双要件模式,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认定规则。对实质性投资的认定需突破单一资金要素,构建“资本投入—智力贡献—效益转化”三维评价模型,实质性投资的类型应涵盖数据获取投入成本(如采集数据的设备成本、人力投入)、数据验证投入成本(包括数据清洗、去噪、标注等全流程劳动)、数据呈现投入成本(数据库结构设计、可视化工具开发等)。商业价值认定则需建立“现实收益+潜在价值”双层评估体系,现实收益应当包括直接收益(数据销售/许可收入、数据产品利润占比等)与间接收益(数据驱动的业务增长,如广告转化率、竞争优势、市场占有率的增加等);潜在价值应涵括数据在未来的应用场景(如基因数据对药物研发的价值等)中的适用前景。为避免裁判尺度不一,实质性投资及商业价值的认定规则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如实质性投资从投资规模来看需达到“显著”程度,从投资必要性来看应与数据质量提升或价值挖掘直接相关。而对商业价值的评估,从市场验证来看,需证明数据已被实际用于商业活动或存在明确市场需求;从可量化性角度审视,则应提供收益计算模型或相关案例等作为参考。
第二,进一步明确赔偿计算指引。数据要素的非物质性和价值衍生性往往会造成数据侵权损害赔偿缺乏可操作的量化标准,实践中多适用法定赔偿标准,各地司法裁量的标准存在不统一的情况。对此,笔者认为,可通过区别数据权益类型与具体侵权行为,探索建立“分类定责+技术量化”的赔偿计算逻辑,以突破对法定赔偿的路径依赖。具体而言,如涉及著作权的,可按照创作成本与市场收益作为赔偿量化依据;在商业秘密类案件中,可采取直接损失与竞争优势折损作为赔偿计算依据;在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则可以综合考量行为危害量化、市场秩序损害等作为赔偿计算的考量因素。在分类的基础上,还可借鉴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技术贡献率”的有关规定,通过量化数据要素在整体产品或服务中的价值贡献比例,推行技术鉴定标准化报告、恶意侵权惩罚性赔偿,并在结合侵权人获利情况的基础上,科学确定此类案件的赔偿数额。
第三,尝试适用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数据加工流程的复杂性使得技术事实的认定存在困难。对此,可尝试组建“数据技术专家库”,在复杂案件中指派技术调查官就技术事实发表专业意见、协助核算贡献率等。如在四川成都某智能公司诉成都某软件公司软件侵权一案中,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表明被诉侵权产品并未侵权。但是,该案技术调查官在查清软件代码的详细结构、顺序组织等事实后,确定鉴定意见书中部分技术事实认定有瑕疵,并提出了相应专业意见。法院结合技术调查官的比对意见,认定鉴定结论存在错误,并不予采纳。此外,还可以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帮助技术事实查明。如引入数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数据价值贡献专项审计报告》,作为裁判参考。
第四,合理进行举证责任配置。数据侵权隐蔽性强致使权利人举证困难。因此,还应灵活适用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依据案件具体情况要求侵权方就其手段合法性进行举证,以此实现个案平衡,保障各方合法权益。例如,在北京某公司诉上海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获取方对自身技术使用情况更具举证优势,当运营方已穷尽手段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获取方采用不当技术获取数据具有高度可能性时,举证责任应向数据获取方转移,由其对技术手段的合法性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据。
综上所述,通过上述治理规则的探索建构,进一步破解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局,在数据流通效率与权益保障间实现动态平衡。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建构,实质上是技术理性与法律价值的动态调适过程。本文通过参考司法裁判中的裁判样本,展现了“场景识别—分类保护”的裁判范式。在数据立法时机尚未到来之际,司法可在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内,通过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规制、《著作权法》对数据库产品的有限保护、商业秘密规则对技术的保护,在现行框架内实现数据治理的效率最大化,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治理规则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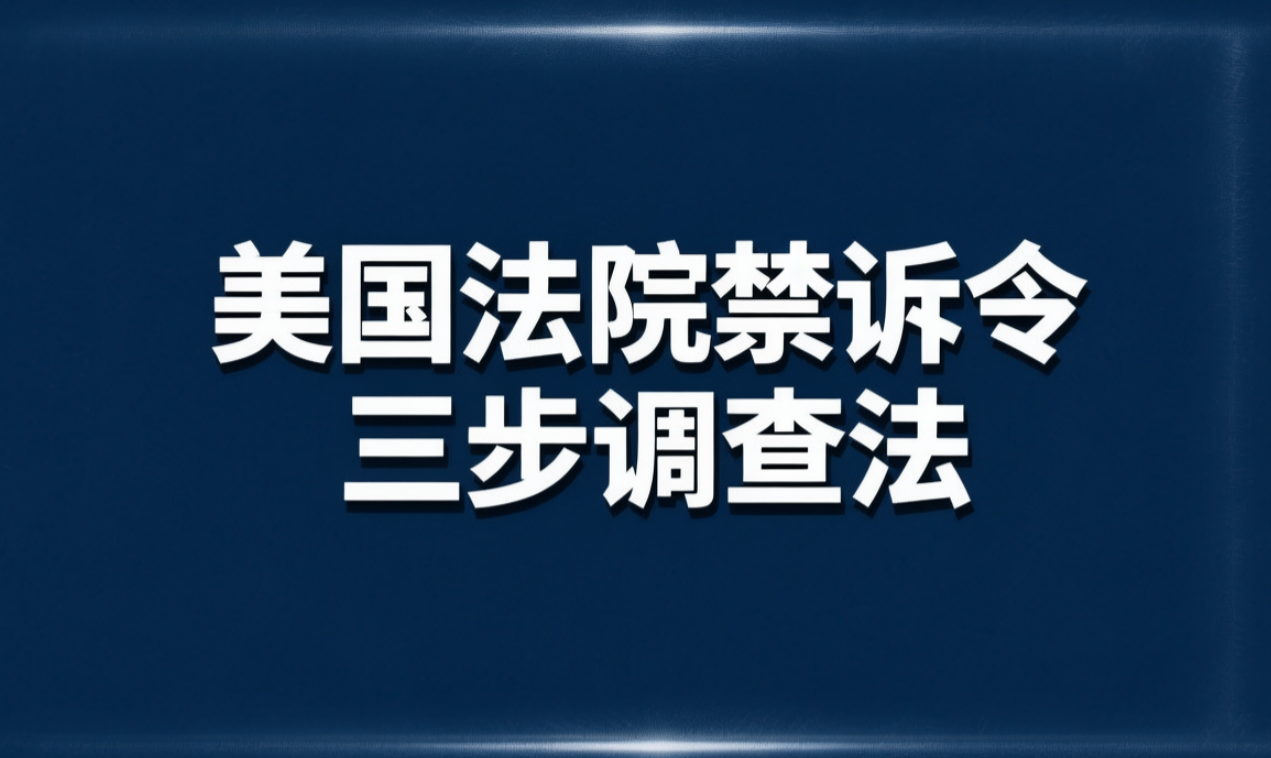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上一篇
上一篇 





评论